更新时间:2023-09-01 14:04
详细剧情
其貌不扬的美术馆警卫亚当成了一名艺术系女学生的期末作业,她野心勃勃要让他从头到脚彻底改头换面……
长篇影评
1 ) 文化发展的缩影
其实相对于《人体雕像》,个人更喜欢《追求不朽的人》这个译名。因为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这个看似平淡的译名更多的揭示了影片的内涵。虽然还没有欣赏过导演乔治 巴勒菲的处女作《田园春光》,但从其第二部作品中,我们却可以感受到导演高超的掌控能力和对于文化与影像的壮志雄心,当然,怪诞与诡异也会随着影片的逐渐流行被大家树立为导演的风格与标志。
影片由典型的三段式构成,但这并不意味着导演对于奇巧结构的迷恋,而仅仅是服务于导演对于所谓的某种文化进阶性的诠释。三段影像分别对应于人类的三种典型文化现象,性 ,食 ,艺术。通过对于文化发展史的剥离与筛选,导演触摸到了人类文化的脉络。
对于观众来说,影片中性与食影像片段之间的割尾巴行为虽然有着一种强烈的文化进化的象征,但是这两段影像却是可以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的。性交与饮食作为人类文化的两大支柱,是一切人类文化的起源。正如列维 施特劳斯所说:人类社会和文化是以性和食为两大主轴,以二元对立的基本模式,并在人类语言和人类思想同步发展的基础上被建构起来的。影片对性与食的表现,同时表现了自然和文化两大成分。性的关系与食物,是人类最早的祖先从自然分离出来,而向文化过渡过程中所创造的最初文化。而在那时,人类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人类本身的生存与繁殖以及吃饱肚子,在这其中,性与食却指向两种不同的文化,性,虽然有着一种繁殖后代的功利需要,但是,更多时候,性却是感官上的自然化的愉悦释放,性扮演着精神文化生产的角色 。而这却不同于食 ,食更多是物质文化生产。因此,影片中对于对于压迫的性与强迫的食的描写正好印证了福柯关于性与权力的论述,福柯认为:在传统权力观念里,性完全被视为繁衍后代的严肃事情,人们对于性一般要保持缄默。权力对于性,就是禁止、拒绝和否定。而对于食却是弘扬,接受和肯定。更深层次的,性与食的对立揭示了的权力运作下人类文化发展的根本问题 ,那就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不同发展,在权力机制下,通过各种规则对性压迫对食强迫。造成了 文化再生产的不平衡 ,但这种权利的运作却不是消极而退步的 ,作为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 。他直接促成了文化发展的下一阶段,艺术的形成 。从古至今,艺术都被看作是在感性愉悦下沐浴真理光辉的桥梁,因此作为文化发展不平衡的产物,艺术起到了某种弥补裂痕的作用 。通过对于感性的肯定 ,艺术加强了精神文化的发展。无论是弗洛伊德的关于艺术是性和无意识 ,还是海德格尔的艺术是自行置入作品的真理。都可以看出艺术的作用。但是随着艺术亦或是文化的发展,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却格格不入起来。这是因为随着艺术的逐渐自律,艺术逐渐与日常生活分道扬镳。在对物质世界的陈腐与庸俗的批判过程中,艺术逐渐变成了一种孤芳自赏的游戏。在影片的第三段中,作为艺术家的 主人公得不到爱情的滋润,就是艺术与日常生活陌生化的一种表现. 这种陌生化将会导致艺术的更加激进,影片中将婴儿作为艺术品的段落可以在艺术发展史中找到原型-先锋派,到了影片结尾,主人公将自身做成人体雕像,艺术的先锋化达到了极致。而此时,一种悖论产生了 ,需要有人认同的艺术却走向抛弃认同者的道路,这种极端的文化会得到认同吗?这是艺术的终结吗 ? 在影片结尾 ,导演隐约给出了答案,在那个隐喻着未来的超现实主义博物馆,主人公的人体雕像被人顶礼膜拜,先锋化被认同了 。
影片由典型的三段式构成,但这并不意味着导演对于奇巧结构的迷恋,而仅仅是服务于导演对于所谓的某种文化进阶性的诠释。三段影像分别对应于人类的三种典型文化现象,性 ,食 ,艺术。通过对于文化发展史的剥离与筛选,导演触摸到了人类文化的脉络。
对于观众来说,影片中性与食影像片段之间的割尾巴行为虽然有着一种强烈的文化进化的象征,但是这两段影像却是可以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的。性交与饮食作为人类文化的两大支柱,是一切人类文化的起源。正如列维 施特劳斯所说:人类社会和文化是以性和食为两大主轴,以二元对立的基本模式,并在人类语言和人类思想同步发展的基础上被建构起来的。影片对性与食的表现,同时表现了自然和文化两大成分。性的关系与食物,是人类最早的祖先从自然分离出来,而向文化过渡过程中所创造的最初文化。而在那时,人类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人类本身的生存与繁殖以及吃饱肚子,在这其中,性与食却指向两种不同的文化,性,虽然有着一种繁殖后代的功利需要,但是,更多时候,性却是感官上的自然化的愉悦释放,性扮演着精神文化生产的角色 。而这却不同于食 ,食更多是物质文化生产。因此,影片中对于对于压迫的性与强迫的食的描写正好印证了福柯关于性与权力的论述,福柯认为:在传统权力观念里,性完全被视为繁衍后代的严肃事情,人们对于性一般要保持缄默。权力对于性,就是禁止、拒绝和否定。而对于食却是弘扬,接受和肯定。更深层次的,性与食的对立揭示了的权力运作下人类文化发展的根本问题 ,那就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不同发展,在权力机制下,通过各种规则对性压迫对食强迫。造成了 文化再生产的不平衡 ,但这种权利的运作却不是消极而退步的 ,作为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 。他直接促成了文化发展的下一阶段,艺术的形成 。从古至今,艺术都被看作是在感性愉悦下沐浴真理光辉的桥梁,因此作为文化发展不平衡的产物,艺术起到了某种弥补裂痕的作用 。通过对于感性的肯定 ,艺术加强了精神文化的发展。无论是弗洛伊德的关于艺术是性和无意识 ,还是海德格尔的艺术是自行置入作品的真理。都可以看出艺术的作用。但是随着艺术亦或是文化的发展,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却格格不入起来。这是因为随着艺术的逐渐自律,艺术逐渐与日常生活分道扬镳。在对物质世界的陈腐与庸俗的批判过程中,艺术逐渐变成了一种孤芳自赏的游戏。在影片的第三段中,作为艺术家的 主人公得不到爱情的滋润,就是艺术与日常生活陌生化的一种表现. 这种陌生化将会导致艺术的更加激进,影片中将婴儿作为艺术品的段落可以在艺术发展史中找到原型-先锋派,到了影片结尾,主人公将自身做成人体雕像,艺术的先锋化达到了极致。而此时,一种悖论产生了 ,需要有人认同的艺术却走向抛弃认同者的道路,这种极端的文化会得到认同吗?这是艺术的终结吗 ? 在影片结尾 ,导演隐约给出了答案,在那个隐喻着未来的超现实主义博物馆,主人公的人体雕像被人顶礼膜拜,先锋化被认同了 。
2 ) 【追求不朽的人】-匈牙利导演乔治•巴勒菲2006年影片
这是第一次看匈牙利的当代影片,《追求不朽的人》给我的感觉就是一部《地下》,喧闹、荒诞、戏谑、残酷,当然还有对社会主义政治神话的反讽,残酷的写真乃至绝望的荒诞。而导演乔治·巴勒菲跟库斯图里卡仿佛一类艺术家,气质颇为相近。同时,他也达到了马尔克斯那本《百年孤独》中的历史维度,侧身望向后方的虚空……
2006年匈牙利电影节的最佳影片《Taxidermia》(中译《人体雕像》、《百年癫狂》、《追求不朽的人》),戛纳电影节最争议的电影,评论也如是:magnificent provided you can stomach it。看过电影后就会觉得这句评价实在恰如其分。一部看完一小时后仍想呕吐的电影,但却是一部相当深刻乃至精彩的电影。这样的评价应该足以显示出电影本身的张力了。是一部很奇特并且很耐人寻味的影片。影片采用三段叙事的情节结构,配以略带超现实风格的影像,向我们讲述了历经匈牙利不同历史时代的祖孙三代之间的故事。与以往同类型影片宏观的展现历史进程与个体成长休戚相关的演变过程不同,《人体雕像》始终将描述的重点聚焦在了更为深层次的“人性”问题上,并对其进行了深度的挖掘整部影片堪称怪诞现实主义的直接呈现:以肉身为中心,暴食、呕吐、排泄、交媾、手淫、自虐……种种生理机能被强调到极致,给人极大的冲击。在这里,我想到了同为异端的帕索里尼那部《索多玛120天》。因为身体成为是匿名的、无形的结构性权力的支配客体,是体制化的机器,也是无路可退的个人的最后和唯一的反抗凭借,无不透出逼人的森冷。那是没有了任何政治许诺和宗教抚慰的最孤独的寒冷——成为驯服的机器,或者使它呈现个人意识色彩死亡。一场关于统治/服从/反抗的身体\政治的寓言。
电影由祖父、父亲、儿子三部分组成,分别代表了匈牙利三个历史阶段,即二战时期、社会主义时期和后社会主义时期。第一个故事名为“Sperm”,意为“精液”。祖父是军官,享有支配权威,他对权力的使用,是漫溢性的,肆意突破应有的界限,从而形成对下属的全权专制。故事的主人公是二战时期一名匈牙利军官的年轻男仆,虽然对异性有着近乎疯狂的欲望,在性欲的驱使下,他用打火机、冰水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手段刺激自己的性器官;他忘情的吮吸两位女性的洗澡水;他一边偷看着两位女性嬉戏一边自慰;他把一堆鲜活的猪肉幻想成女性的胴体……规则和纪律把莫索洛夫塑造和建构为一个驯服的身体,严格地按给定的规范出现在特定的时间空间里——几点起床,几点操练,几点为长官烧洗澡热水,几点做早餐…然后,还要几点喂猪,最后,几点回小屋睡觉。位置的常规化意味着时空的固定化,狭小得像鸟笼一样不自由。但即使这样,反叛的暗流也在涌动,反叛的动力来自身体——身体的欲望冲动——高度个人化的心理补偿,对自我的救赎——总要试图突破一切规范制度的障碍,寻求快感满足。莫索洛夫的欲望对象,是军官的两个女儿及其肥硕的老婆(她们是军营仅有的异性)——两女儿享用完他烧好的洗澡水后,他弯下腰,把头深埋入脏水中,贪婪地吸嗅着——多么粗鄙而有力的色情表现啊!卑微个人的灰色生存方式还体现在每个夜晚,在肮脏狭小的空间,上演的就是一场场自慰的狂欢表演——影片一开头,就充满了淫亵的意味:他吻火,用蜡烛烧烤身体各性感带,以获得更大刺激,最后,生殖器竟隐喻性地喷火出来(多么肆无忌惮的夸张啊)。肉身冲动逼迫他屡屡突破“不许偷窥”的规训,她们的每一缕气息,每一次笑声,每一寸肌肤,都成为疯狂的引诱,挑逗起自慰行为——他把器官伸入一涂了油脂的墙洞,伸缩间给一大公鸡好奇地猛啄一口,惨叫中一切嘠然而止——让人笑都笑不出来的沉重黑色幽默。逻辑似乎是这样的:底层者被剥夺了对象性满足的所有可能,被压迫着从外界世界驱赶回自身身体,依靠想象或对满足经验的回忆获得快感享用。虽然无奈,但毕竟还有一小快空间,行使破碎主体最后的自由——把身体作为快乐的生产机器而非被奴役的器具。影片对这种卑微的自由保持着一种残酷的反讽透过在军士慌张穿裤子时背后一声枪响,死在了那一堆被他凌辱过的猪的尸体上以再现这种对人性本能的集权暴力!
影片第二个故事“Saliva”(意为唾液)所讲的食欲问题。父亲出生时,给祖父(军官)夹去了一条小猪尾巴。这无疑是一个身体隐喻和转换。事实证明,他确实是社会主义所圈养的一头猪。韦伯论述过,社会主义社会并不能消除甚至减轻人的异化,相反,它会因为强化科层制而导致异化的加深——社会主义完全控制了整个经济结构,将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严格规范化和标准化,并通过科学技术手段,加强对个人的控制。如葛兰西所说,它绑架了整个民主生活。这种极度的官僚专制的实质就是全权控制的极权主义。每个普通人,都是社会主义生产机器上的一个劳动部件,无一例外地被纳入手段—目的的整体链中。父亲的命运是这样被给定的:为了国家荣誉(虚构奥运会将设立速食竞赛项目),父亲必须被训练和培养为食量惊人且进食速度惊人的大胃王,除了比赛,他们还可以为建国几十周年的节日助兴,通过疯狂的吃这一举动和雍胖的身体来炫耀唯物主义的胜利,显示社会主义是物产丰富的天堂。他和他们,还有他的老婆不停地吃,然后,又通过药物把刚吃下的东西呕吐出来。反人道的荒谬行径是因为他们仅仅被当作体制话语的器具。相比勤务兵,他们更为悲惨,因为自身对其身体的基本控制如进食自由都被剥夺。到了他的晚年,已经是后社会主义时期,他已成为一不能行动的肉,还在不停地吃,不停地看着电视上奥运会速食赛,抱怨自己壮志未酬,未能获得崇高荣誉以实现人生的最大价值。你不禁会为人被政治奴役和塑造的极端而惊愕。第二个时代是一个虚胖"猪"的时代,这里的吃饭都不是描写的食欲,吃是一种运动,一种"大跃进"式表演,一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虚华竞赛,最后造成的是身体的(经济)跨掉。
第三段是“Blood”,但影片讲述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凶杀、暴力之类的故事,而是探讨了“永恒与不朽”这一话题。主角是儿子。他出奇地瘦,仿佛是一个对其父过度或矫枉过正的否定,而且,更吊诡的是,他的职业竟是一名标本制作师。他每周去看一次父亲,带去食物并打扫,顺便照顾几只肥胖无比的竞食猫;他对一女收银员有好感,这也许是他忍受世界的一个理由。他和父亲爆发冲突的几周后他去买东西看父亲,收银员换成了男的,世界一下子暗淡了下来;到家后发现父亲已死去,直肠和内脏被掏了出来,狼藉满地,血与粪凃满了猫的嘴脸。他把父亲制作成一个标本,永生的艺术品。接下来他因为失望感与负罪感自杀了。他冷静地用刀剖开身体,我们的眼前展开了一场解剖学的视觉盛宴——惨白皮肤下的鲜红肌肉(和猪肉好象没什么区别),筋脉,然后,把内脏一个个取出,然后,用线把空躯体缝合,最后,固定,一把锋利的刀带着华丽的风声干净利落地把头砍下。影片结束部分,我们看到了博物馆中的艺术品:一件无头的、断臂的希腊式的人体塑像。这当然是最后的一个隐喻:没有思想(被砍掉了头颅)、没有行动能力(手臂的断去)被理性的政治话语所绞杀、阉割、压抑和机械的暴力作用下人的生存意象。这是一种追加递进的反抗,使其成为一件“体制的标本”。建立在完整的自我意识和自我理解上,这种身体的自我反思和改造克服了死亡恐惧的保守怯懦,在一系列自我设计和惩罚之后,取得了最后解放。第三个时代是后遗症时代,解体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下子变成一个尴尬的没有人喜欢的畸型瘦子,每天面对变成一堆肥肉靠回忆过日子的父亲。在这样的情况下,把父亲和自己都做成供别人研究的标本.成为历史的不朽的标本。
此片是艺术、现实与思想的绝妙结合,导演将这几部分融合的非常好,他运用的工具有:性与身体的政治隐喻、荒诞叙事、从极权社会到后极权的图景式演变、偏执而奇异的想象力、完美的三段式结构、从卡夫卡到杨史云梅耶的东欧艺术血脉。这些元素的运用使得影片的荒诞现实主义风格可谓淋漓尽致:喷火的阳具,射向天空变成星星的精液,极端欲望导致的荒诞幻觉,卖火柴的小女孩在童话书中复活,然后憧憬星空,还有婴儿制成的琥珀般的吊坠艺术品......还有类似于表现主义惯用的酷烈画面:竞吃运动员肉山般的身体,竞吃猫肯吃人体内脏的凶残,鲜活的蠕动的跳跃的血淋淋的人体内脏的切割,纯白色人体雕像展厅一身袭白的围观者,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电影结束在一个超现代的艺术馆里,建筑是白色的,观众穿着白色的衣服,观赏着父与子的人体雕像,听着解说词:“这是最主要的……当然,每个人对什么比较重要有自己的看法…对一些人来说,是空间;对另一些人来说,是时间……”。
(注:文中部分文字和资料来自各位网友的视频评论,做了修改和删除。)
2006年匈牙利电影节的最佳影片《Taxidermia》(中译《人体雕像》、《百年癫狂》、《追求不朽的人》),戛纳电影节最争议的电影,评论也如是:magnificent provided you can stomach it。看过电影后就会觉得这句评价实在恰如其分。一部看完一小时后仍想呕吐的电影,但却是一部相当深刻乃至精彩的电影。这样的评价应该足以显示出电影本身的张力了。是一部很奇特并且很耐人寻味的影片。影片采用三段叙事的情节结构,配以略带超现实风格的影像,向我们讲述了历经匈牙利不同历史时代的祖孙三代之间的故事。与以往同类型影片宏观的展现历史进程与个体成长休戚相关的演变过程不同,《人体雕像》始终将描述的重点聚焦在了更为深层次的“人性”问题上,并对其进行了深度的挖掘整部影片堪称怪诞现实主义的直接呈现:以肉身为中心,暴食、呕吐、排泄、交媾、手淫、自虐……种种生理机能被强调到极致,给人极大的冲击。在这里,我想到了同为异端的帕索里尼那部《索多玛120天》。因为身体成为是匿名的、无形的结构性权力的支配客体,是体制化的机器,也是无路可退的个人的最后和唯一的反抗凭借,无不透出逼人的森冷。那是没有了任何政治许诺和宗教抚慰的最孤独的寒冷——成为驯服的机器,或者使它呈现个人意识色彩死亡。一场关于统治/服从/反抗的身体\政治的寓言。
电影由祖父、父亲、儿子三部分组成,分别代表了匈牙利三个历史阶段,即二战时期、社会主义时期和后社会主义时期。第一个故事名为“Sperm”,意为“精液”。祖父是军官,享有支配权威,他对权力的使用,是漫溢性的,肆意突破应有的界限,从而形成对下属的全权专制。故事的主人公是二战时期一名匈牙利军官的年轻男仆,虽然对异性有着近乎疯狂的欲望,在性欲的驱使下,他用打火机、冰水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手段刺激自己的性器官;他忘情的吮吸两位女性的洗澡水;他一边偷看着两位女性嬉戏一边自慰;他把一堆鲜活的猪肉幻想成女性的胴体……规则和纪律把莫索洛夫塑造和建构为一个驯服的身体,严格地按给定的规范出现在特定的时间空间里——几点起床,几点操练,几点为长官烧洗澡热水,几点做早餐…然后,还要几点喂猪,最后,几点回小屋睡觉。位置的常规化意味着时空的固定化,狭小得像鸟笼一样不自由。但即使这样,反叛的暗流也在涌动,反叛的动力来自身体——身体的欲望冲动——高度个人化的心理补偿,对自我的救赎——总要试图突破一切规范制度的障碍,寻求快感满足。莫索洛夫的欲望对象,是军官的两个女儿及其肥硕的老婆(她们是军营仅有的异性)——两女儿享用完他烧好的洗澡水后,他弯下腰,把头深埋入脏水中,贪婪地吸嗅着——多么粗鄙而有力的色情表现啊!卑微个人的灰色生存方式还体现在每个夜晚,在肮脏狭小的空间,上演的就是一场场自慰的狂欢表演——影片一开头,就充满了淫亵的意味:他吻火,用蜡烛烧烤身体各性感带,以获得更大刺激,最后,生殖器竟隐喻性地喷火出来(多么肆无忌惮的夸张啊)。肉身冲动逼迫他屡屡突破“不许偷窥”的规训,她们的每一缕气息,每一次笑声,每一寸肌肤,都成为疯狂的引诱,挑逗起自慰行为——他把器官伸入一涂了油脂的墙洞,伸缩间给一大公鸡好奇地猛啄一口,惨叫中一切嘠然而止——让人笑都笑不出来的沉重黑色幽默。逻辑似乎是这样的:底层者被剥夺了对象性满足的所有可能,被压迫着从外界世界驱赶回自身身体,依靠想象或对满足经验的回忆获得快感享用。虽然无奈,但毕竟还有一小快空间,行使破碎主体最后的自由——把身体作为快乐的生产机器而非被奴役的器具。影片对这种卑微的自由保持着一种残酷的反讽透过在军士慌张穿裤子时背后一声枪响,死在了那一堆被他凌辱过的猪的尸体上以再现这种对人性本能的集权暴力!
影片第二个故事“Saliva”(意为唾液)所讲的食欲问题。父亲出生时,给祖父(军官)夹去了一条小猪尾巴。这无疑是一个身体隐喻和转换。事实证明,他确实是社会主义所圈养的一头猪。韦伯论述过,社会主义社会并不能消除甚至减轻人的异化,相反,它会因为强化科层制而导致异化的加深——社会主义完全控制了整个经济结构,将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严格规范化和标准化,并通过科学技术手段,加强对个人的控制。如葛兰西所说,它绑架了整个民主生活。这种极度的官僚专制的实质就是全权控制的极权主义。每个普通人,都是社会主义生产机器上的一个劳动部件,无一例外地被纳入手段—目的的整体链中。父亲的命运是这样被给定的:为了国家荣誉(虚构奥运会将设立速食竞赛项目),父亲必须被训练和培养为食量惊人且进食速度惊人的大胃王,除了比赛,他们还可以为建国几十周年的节日助兴,通过疯狂的吃这一举动和雍胖的身体来炫耀唯物主义的胜利,显示社会主义是物产丰富的天堂。他和他们,还有他的老婆不停地吃,然后,又通过药物把刚吃下的东西呕吐出来。反人道的荒谬行径是因为他们仅仅被当作体制话语的器具。相比勤务兵,他们更为悲惨,因为自身对其身体的基本控制如进食自由都被剥夺。到了他的晚年,已经是后社会主义时期,他已成为一不能行动的肉,还在不停地吃,不停地看着电视上奥运会速食赛,抱怨自己壮志未酬,未能获得崇高荣誉以实现人生的最大价值。你不禁会为人被政治奴役和塑造的极端而惊愕。第二个时代是一个虚胖"猪"的时代,这里的吃饭都不是描写的食欲,吃是一种运动,一种"大跃进"式表演,一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虚华竞赛,最后造成的是身体的(经济)跨掉。
第三段是“Blood”,但影片讲述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凶杀、暴力之类的故事,而是探讨了“永恒与不朽”这一话题。主角是儿子。他出奇地瘦,仿佛是一个对其父过度或矫枉过正的否定,而且,更吊诡的是,他的职业竟是一名标本制作师。他每周去看一次父亲,带去食物并打扫,顺便照顾几只肥胖无比的竞食猫;他对一女收银员有好感,这也许是他忍受世界的一个理由。他和父亲爆发冲突的几周后他去买东西看父亲,收银员换成了男的,世界一下子暗淡了下来;到家后发现父亲已死去,直肠和内脏被掏了出来,狼藉满地,血与粪凃满了猫的嘴脸。他把父亲制作成一个标本,永生的艺术品。接下来他因为失望感与负罪感自杀了。他冷静地用刀剖开身体,我们的眼前展开了一场解剖学的视觉盛宴——惨白皮肤下的鲜红肌肉(和猪肉好象没什么区别),筋脉,然后,把内脏一个个取出,然后,用线把空躯体缝合,最后,固定,一把锋利的刀带着华丽的风声干净利落地把头砍下。影片结束部分,我们看到了博物馆中的艺术品:一件无头的、断臂的希腊式的人体塑像。这当然是最后的一个隐喻:没有思想(被砍掉了头颅)、没有行动能力(手臂的断去)被理性的政治话语所绞杀、阉割、压抑和机械的暴力作用下人的生存意象。这是一种追加递进的反抗,使其成为一件“体制的标本”。建立在完整的自我意识和自我理解上,这种身体的自我反思和改造克服了死亡恐惧的保守怯懦,在一系列自我设计和惩罚之后,取得了最后解放。第三个时代是后遗症时代,解体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下子变成一个尴尬的没有人喜欢的畸型瘦子,每天面对变成一堆肥肉靠回忆过日子的父亲。在这样的情况下,把父亲和自己都做成供别人研究的标本.成为历史的不朽的标本。
此片是艺术、现实与思想的绝妙结合,导演将这几部分融合的非常好,他运用的工具有:性与身体的政治隐喻、荒诞叙事、从极权社会到后极权的图景式演变、偏执而奇异的想象力、完美的三段式结构、从卡夫卡到杨史云梅耶的东欧艺术血脉。这些元素的运用使得影片的荒诞现实主义风格可谓淋漓尽致:喷火的阳具,射向天空变成星星的精液,极端欲望导致的荒诞幻觉,卖火柴的小女孩在童话书中复活,然后憧憬星空,还有婴儿制成的琥珀般的吊坠艺术品......还有类似于表现主义惯用的酷烈画面:竞吃运动员肉山般的身体,竞吃猫肯吃人体内脏的凶残,鲜活的蠕动的跳跃的血淋淋的人体内脏的切割,纯白色人体雕像展厅一身袭白的围观者,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电影结束在一个超现代的艺术馆里,建筑是白色的,观众穿着白色的衣服,观赏着父与子的人体雕像,听着解说词:“这是最主要的……当然,每个人对什么比较重要有自己的看法…对一些人来说,是空间;对另一些人来说,是时间……”。
(注:文中部分文字和资料来自各位网友的视频评论,做了修改和删除。)
3 ) 释放欲望与收缩精神是一样的
乔治·巴勒菲的电影《人体雕像》对匈牙利以及东欧历史的隐喻和讽刺,是显而易见的,对此不作赘述,今天想讨论的,主要是电影中祖孙三代主角身上的两条延续不断的线索:肉体/欲望的极端释放,与精神/自我的极端收缩——这两条线索构成如DNA双螺旋一样的结构,刺击所有现代人优越而可疑的存在感。
电影的剧情大概是:战时的下等兵马洛戈瓦伊长相丑陋,生活在机械刻板和长官压制之下,马洛戈瓦伊旺盛的性欲亦受到压制无处释放,便沉浸在偷窥时手淫、以烛火灼皮的猥琐行为和对各种女性的性幻想里,终而恍惚间奸淫母猪尸体并被长官击毙。马洛戈瓦伊与长官妻子偷情而生下长猪尾的儿子卡勒马·巴拉托尼,卡勒马自小被送去练习暴食因此肥胖不堪,而后代表匈牙利参加社会主义暴食大赛,并成为世界冠军,期间结识同为暴食者的妻子,生下儿子拉尤斯·巴拉托尼。拉尤斯是一个极为瘦弱的动物标本匠人,生活主题是制作标本和赡养已肥胖而无法挪动的老卡勒马。最后,拉尤斯将意外死亡的父亲制作成人体标本,并设计一套自动装置,将自己身体切割并制成人体雕像。
从马洛戈瓦伊的欲望受压致死,到卡勒马暴食而肥胖丑陋,到瘦弱的拉尤斯对通俗肉体的极端反感和厌弃,乔治·巴勒菲通过对祖孙三代身体形态异变的串述,呈现了这个“挤压”-“释放”-“迷失”的传奇故事,仿佛吹爆一枚硬气球的过程:拉尤斯和卡勒马残存的尸体成为人体雕像,如同气球爆裂后的碎片,仍然存于世界,供旁观者揣想其历程和意义,但结论似乎只能是虚无——从极端的肉体压制中释放出来,人将迷失于极端的虚胖和虚瘦中。
这种极端状况导致的无尽虚空,在精神上也同样作用于人:马洛戈瓦伊在压制之中,其精神需求和自我感知是极其明确而强烈的,而卡勒马在衣食无忧、精神受到意识形态绑架的生活下,自我仅仅附着于虚华的名利,他存在的内核所剩无几了,直到拉尤斯,他并不生活在表面的物质和精神自由里,而是在父辈和历史的阴影之下,饕餮老父的臃肿肉体和因对这肉体形态的应激性反感而产生的自我否定,让他更失精神内核,陷于虚无及其未知之中,无所依附。自我或精神的完整性在三代人的身上逐渐收缩至无、至死亡的最终领域。
虚无之后,我们将如何看待这个无奈的进程呢?在电影中,拉尤斯和卡勒马的尸体最终被雷古齐教授在地下室里发现,教授将这看作是一项艺术发现,将这一对标本作为艺术品公之于众,并陈述一个看似有所着落的结论:每个人都对什么比较重要有自己的看法,对一些人来说,是空间,对另一些人来说,是时间。
这种堂而皇之的艺术家观念和评价在此显得可笑,它代表的是一种冷漠、麻木的懒惰,在马洛戈瓦伊祖孙三代的经历之中,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感同身受的态度,而非懒散的局外人视角,因为这一夸张而极端的变异,在每一个现代人身上都在或快或慢地发生着,乔治·巴勒菲这部电影的伟大之处,也绝非在题材、艺术手法和讽喻性上,而在他如此形象地描述了一种我们遗忘在历史、忽略于过去而现实存在的问题。
最后说一点扩展:拉尤斯的自我切割装置与小松左京的小说《野性之口》的描述有很大的相似,它着力于以这种极端的设定方法去讨论食欲作为一种人的存在属性的尽头在哪里。另外,卡勒马参加的暴食大赛,让我想起了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对奥雷连诺第二在家中举办饕餮比赛的描写,非常相似。不知道乔治·巴勒菲是否受到了二者的启发。下面附上了这两个文本,感兴趣的话可以读读。
=============================
小松左京《野性之口》:
完全没有理由。
为什么需要一个理由呢?人们总想要为每一件事都找出理由,可真理是永远无法解释的。所有的存在为什么是现存的样态?为什么是以这种方式而不是别的方式存在?
那种理由,还没有任何人可以解答。
他望着窗外磨牙,胸中怒火熊熊。有时候,这种愤怒突然之间就把他淹没了,在他躯体的中心弥漫着一种剧烈的无理性的冲动,一种无法对任何人解释的毁灭的冲动。他猛地拉上窗帘,用力吸气、收紧肩膀,然后回到里屋。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毫无价值、荒谬可笑的。活着是一件荒唐无益的事情。首先,这个毫无价值的玩意儿——我自己——就荒谬得让人无法忍受。
为什么这样荒谬?
“为什么?”——还是这个问题。
毫无价值,荒谬可笑,仅仅因为它就是这样。每件事——财产、科学、爱情、性、生活,老于世故的人——自然、地球、宇宙——所有令人作呕的污秽,让人沮丧的愚蠢。所以——
不。根本不是所以,而是无论如何,我真的要去做那件事。
我要去做。他无声地喊:我确实要。
当然,这将和别的事一样愚蠢——事实上,在一切各式各样的蠢事中间,也许是最愚蠢的?但至少这件事有那么一点刺激——一种锐利的感觉。也许这个详细周全的计划的核心就是一种疯狂的尝试?也许是这样,但至少——
我就要开始做的这件事是任何人在头脑正常的时候从未尝试过的。
毁灭世界?历史上有千千万万人有过这样的狂想。而他这个想法不是那么陈旧的。不可能有更荒谬的想法了,只有它才能扑灭他心头的怒火。我内心的火焰被一种高贵的绝望扇起来了……
进入内室,他锁上门,打开灯。现在——这想法使他两眼放光——现在开始了。
清冷的光线照亮了房间。一个角落里摆着一台家用电烤箱;一组煤气灶、一部切片机、大大小小的平底锅、一套刀具、一个装满各种调味料和蔬菜的壁橱。旁边是一个自动工作台,设置了全套程序,可以进行人类有史以来对身体进行过的任何外科手术——不管是难度多大、多么复杂的手术,即使是最大的医院里才能做的,这里也都能完成。手术台旁边,是一些假肢:手、脚;任何一种最先进的人造器官。
万事具备。他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去策划细节,又花了一个月准备工具。据他推算,作好全部准备至少又多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好,那么——让我们开始吧。
他脱下裤子,爬上手术台,把控制器的许多电极接在身上,扭开摄像机。
开始了——
他用一种戏剧化的姿势拿起手术台支架上的注射器,检查压力刻度,调整设置——调高了一点,因为这是第一次注射——然后把禁用的麻醉剂注射进他右大腿。
大约过了五分钟,这条腿完全失去了知觉,他扭开了自动手术机。机器运作时吱吱呜呜的声音;自动指示灯熄熄亮亮;他的身体不由自主被向后猛拉,同时黑色的机械手延伸出 多个分支。
桌上凸出的夹子固定住腿的胫部和足踝 。一只钢爪握着一个消毒纱布包往下滑到大腿和骨盆的连接处。
电子解剖刀如丝一般细细地切过皮肤,所过之处非常炽热,几乎没有鲜血流出。切开肌肉组织……露出大动脉……用钳子把肉夹下来……包扎……切除并处理感染的肌肉表面……嗡嗡叫着的轮转机锯条旋转着切向股骨。锯条切中了骨头,那一刹那他闭上了眼睛。
几乎没有什么震动感。当内置钻石头的超高速锯条切过骨头时,只发出了轻微的摩擦声,同时给骨头切面敷上混合的强力酵素。在精确的6分钟内,他的右腿干净利落地同躯干分离了开来。
机器用纱布擦拭他浸透汗水的脸,然后递给他一杯药水。他把药水一口饮尽,深吸了口气。他的脉搏在飞快地上升,更多汗水如雨般涌出。但几乎没有失血,也没有什么近似疼痛的感觉。神经治疗很管用。不需要输血。他吸了一些氧气,以缓解头昏眼花的症状。
他那条和身体分离的右腿直挺挺躺在床上。透过透明塑料的绷带,可以看到:一圈外围包着黄色脂肪的收缩的粉红色肌肉组织、白色的骨骼中心可见黑红色的骨髓。几乎没有流血。他望着这条膝盖骨突出的毛绒绒的玩意,几乎忍不住要歇斯底里地狂笑起来。但是此刻没有笑的时间:还有更多的事需要做。
他休息了片刻以恢复体力,然后发出下一步工作的指令。
机器伸出一条机械手,抓起一条人造腿,把它安在刚才的切割面上;没有扎绷带的肌肉上药以后已经恢复了。人工突触中心的信息终端被与从切割处拉出来的神经叶鞘连在一起。终于,躯干的义肢被用带子和特殊医疗器械牢牢安在残余的大腿骨上。完成了。他试着小心地弯曲这条新腿。
到现在为止一切顺利。他极其小心地站起来:变化使他头昏、摇摇晃晃,但不管怎么说他可以站立也能慢慢走路了。假腿是用某种运动时声音很细微的轻金属制成的。没问题——够好的了——反正大部分时间里他都会坐轮椅的。
他举起自己的右腿从桌子头上放下去。腿太沉,几乎使他蹒跚了一下。他又一次在心里爆发了一阵野蛮的狂笑。我整个一生中一直拖着这些分量来来去去。切下这个肢体使他减轻了多少公斤的体重呢?
“好吧,”他咕哝着说,还在咯咯笑,“够了。现在该把血排干净了。”
他把这一大块肉扛上操作台,剥掉塑料包装,系住脚踝倒吊在天花板上,用他的双手挤压,从切口处放血。
后来,在洗涤槽里冲洗它的时候,上面的毛被水敷湿了,在所有动物的肢体中,它看上去最像一只巨大的蛙腿。他瞪着以古怪的姿势戳出不锈钢洗涤槽的那只脚的脚底心。
我的腿。凸出的膝盖,很难找到合脚鞋子的高脚背,一只运动员的脚上生的脚趾——这是我的腿!他终于再也忍不住了,爆发出一阵恶毒的狂笑,在笑声中痉挛地折起腰。最后,这只见鬼的坚韧的运动员的脚终于完蛋了……
是准备烹调的时候了。
他用大切片刀把这条腿从膝部切成两截,然后开始用一把锋利的猪肉刀剥皮。大腿骨裹着看上去很可口的肉,很是粗壮。当然,这是火腿。筋腱很有韧性;他用硬切片刀切得大汗淋漓,很快在身边垒起了厚厚的带着肌肉膜的肉块。他把大块胫骨处的肉放进装满滚水的大罐子,加上桂皮、丁香、芹菜、洋葱、茴香、藏红花、胡椒粒、其他调料和辛辣的蔬菜一起炖。脚被他丢掉了,只从足踝处刮了些肉下来。他把腿肉中用来做肉排的都切了片、擦了盐和胡椒,并拍打肉片使它们变软。
我会有勇气吃它吗?他突然问自己。结实的肉团总会梗在他咽喉的某处。他真的能够把它咽下去吗?
他咬紧牙关,油一般的汗水流了下来。我会吃的。这和人类一直以来烹制并享用其他有智慧的哺乳动物没有什么不同:母牛和绵羊,那些温和的,无辜的,有着悲伤眼睛的食草动物。原始人甚至吃自己的同类;有些种族直到现代还延续着吃人的习俗。为了吃而杀掉动物——也许这中间有正当的理由。其他食肉动物也不得不靠杀戮生存。但是人类……
从他们存在的那一天起,贯穿人类历史,有多少亿万人被杀掉而连吃也没有吃?和那个相比,这样绝对是清白无罪的。我将不去杀任何别的人。我不会去屠杀可怜的动物。通过这种方法,我自己吃的是我自己的肉。还有哪种别的肉能像这种一样毫无罪过?
煎锅里的油开始噼啪作响。他用颤抖的手抓起一大块肉排,犹豫片刻,把它丢进锅里。噼啪响的脂肪使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香喷喷的味道。他仍在发抖,他把轮椅把手握得太紧,几乎要把它折短了。
好吧。我是一只猪。或者,人类比猪要糟糕得多:卑鄙,污秽。在我体内有个部分比猪还不如,还有个“高贵”的部分为比猪还不如感到无尽的愤怒。那个高贵的部分将把那比猪还不如的部分吃掉。这件事里有什么让人害怕的东西么?
被烤得金黄松脆的肉排在盘子上滋滋作响。他往上面抹了芥末,配上柠檬和奶油,浇上肉汁。他拿起餐刀的时候,他的手在打颤,餐刀敲在盘子上,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他汗如雨下,用尽全力握住餐刀,切割,用叉子戳起来,然后提心吊胆地把它送进嘴里。
第三天,他截下了左腿。这一只,胫骨和全部表面都被抹上了大量奶油,用烤肉叉叉起来,架在旋转型烤肉架上烤了。至此他已不再恐惧。他发现自己惊人的可口:这个发现使一种混合着愤怒和疯狂的情绪在他心底牢牢扎下了根。
第一周以后,事情越来越艰难了。他不得不切断了自己的下半身。
在轮椅的方便马桶上,他最后一次享受了排泄的乐趣。当他喷射的时候,他大笑了。
看看这肮脏的货色!我排泄的是我自己,在我自己的内脏中储存然后变成粪便!也许这是自我蔑视的最高形式了——或者是自我颂扬的最高形式?
当他失掉了髋骨以下的部分,两条假腿就基本没用了。但他还让它们留在老地方。现在是换下内部器官的时候了,他向机器的电脑咨询:“当我把肠子吃掉之后,还会有食欲吗?”
“它不会受什么影响。”这就是回答。
他抛掉了大肠,把小肠和蔬菜一起炖,把十二指肠做成腊肠。他用人造器官换下了肝脏和肾脏,然后把这两个器官做了小炒。肚子他先放在一边,放在装着营养液的塑料容器中保存。
在第三周的末尾,他换下了他的心和肺,最后,他把自己跳动的心切成细丝油煎:这是连阿兹塔克主持献祭的祭师都无法想象的事情。(注:阿兹塔克人:16世纪西班牙人入侵时期生活在墨西哥中部的印地安人部族)
当他开始把自己的腹部做成餐点时,他开始清醒地意识到:人类是可以在毫无食欲的情况下机械进食的。腹部用酱油浸泡着,加上了大蒜和红辣椒。
在无数各种各样、希奇古怪的被当作食物的产品中,有多少完全与饥饿无关、纯粹是由于好奇而被开发的?即使好奇心得到了满足,人类还是会吃最不可思议的东西,如果他感到饥饿。吃自己同类的肉时,那种愤怒的感觉就像是用牙齿咬碎玻璃杯一样。
食欲的源泉来自于原始的侵略冲动:杀戮和吃食;践踏和粉碎;吞咽和吸收
——那就是野性之口。
到现在,他的咽喉只能与一根管子相连。直接输送到血液的营养来自一个装满营养液的容器。内分泌活动由人造器官完成。在这张嘴的尽头,双臂都被吃完;唯一保留的是颈部以上的部分,而在第五十天头上,面部所有的肌肉几乎都被吃光了;剩下两片嘴唇在安装的弹簧支持下咀嚼。眼球只剩一只,另一只被吞进嘴里嚼掉了。
现在坐在轮椅上的,是和错综复杂的大大小小的管子堆在一块儿的一副骨架,在这副骨架上,唯一留存的是大脑和一张嘴巴。
不……
即使是现在,一只机械手臂正在剥去头皮,用锯条把头盖骨的顶部干净利落地切了下来。
在暴露的小脑上撒上盐巴、胡椒粉和柠檬汁,舀起满满一大勺——我的脑子,想到这是我的小脑。我怎么能尝这个东西呢?难道一个活人能够品尝自己脑浆的滋味吗?
勺子毁坏了灰色的大脑。没有痛苦——大脑皮层没有感觉。但到了这时,机械手舀出一勺勺灰色糊状的东西放到骷髅的嘴里,嘴巴贪婪地吞咽下去时,“味道”已经无法辨别了。
“是杀人案。”警官从屋里走出来时,面对挤满出口处的记者们说,“此外,这是一起残忍、野蛮得难以想象的罪行。罪犯无疑是一个严重的精神病患者。看上去像是某种变态的实验——身体被一块块卸下来,然后装上人工器官……”
警官处理好媒体方面的问题,进了屋,擦去脸上疲惫的汗水。
从焚化炉过来的侦探疑问地看着他。“录像带已经烧毁了,”他说,“但是,你为什么要说这是一次谋杀呢?”
“为了维持社会的美好与和平。”警官做了个深呼吸。“把它宣布为谋杀——指挥一次官方的调查——然后让它成为我的秘密。这次案件——抹去案件中的证据——它们完全是不合常理的。你不能让一个正常的市民看到在一些人心灵深处的疯狂和自我毁灭的欲望。如果我们做了这样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不小心让人们看到了内心寄居的原始的野兽——好吧,你可以肯定会有人学这个人的样。这一种人——你没办法知道他们能做出什么……
“如果广大民众突然了解了这样的东西,人们将对自己的行为失去自信——他们会开始钻入自己灵魂深处的黑暗中。他们会彻底无法理解自己——完全失去控制!
“你看,人类存在的根源是疯狂——所有动物心底的那种盲目的侵略性的冲动。如果人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果有大批人用存在解放或自己管自己之类的口号来表达这种疯狂——那就是人类文明的终结。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法律、武力、或规章来约束,一切将完全失控!
“人们把别的人撕碎,互相残杀,破坏、毁灭,这些征兆已经开始显现——这个人吞下融化的炸药自杀——那个人倒上汽油自焚而死——另一个光天化日之下在城市中心性交。当没再有什么理智的行为可以作为攻击对象,笼中的野兽就开始毁灭自己的心智——”
“啊呀——”
年轻的侦探从正在腐烂的骨架旁跳开。刚才,正当他想把仍然塞在骷髅嘴里的恶臭的勺羹取出来时,那骷髅的牙齿扣下来,咬住了他的食指,咬掉了指尖的一小块肉。
“小心呀,”警官疲惫地说,“一切动物生命的根基就是那张带着如饥似渴的吞噬欲望的嘴巴,巨大的野性之口……”
在那具裸露着大脑的骷髅上,残留的一只眼球开始变松,有力的弹簧替代了消失的肌肉,正在用肿胀的舌头和坚硬的牙齿咯吱咯吱地咀嚼着那块小小的肉屑。
《百年孤独》对于奥雷连诺第二暴食的描写:
家中的生活变得那么严峻,奥雷连诺第二就觉得在佩特娜·柯特家里更舒服了。首先,他借口减轻妻子的负担,把酒宴移到了情妇家里。然后,借口牲畜正在丧失繁殖力,他又把畜栏和马厩迁到她那儿去了。最后,借口情妇家里不那么热,他甚至把经营买卖的小账房搬到了那儿。菲兰达发现自己变成了守活寡的妇人,时间已经迟了。奥雷连诺第二几乎不在家里吃饭,只是假装回家过夜,但这是骗不了人的。有一天早晨他不小心,有人发现他在佩特娜·柯特床上,然而出乎意外,他不仅没有听到妻子的一小点责备,甚至没有听到她最轻微的怨声,但是就在那一天,菲兰达把他的两口衣箱送到他的情妇家里。她是叫人大白天经过街道中间送去的,让全镇的人都能看见,以为不走正道的丈夫忍受不了耻辱,会弯着脖子回到窝里,可是这个勇敢的姿态只是再一次证明,菲兰达不熟悉丈夫的性格和马孔多的风习,这里的习俗和她父母的旧习毫无共同之处——每一个看见箱子的人都说,这是故事的自然结局,故事的内情是人人皆知的。奥雷连诺第二却举办了三天的酒宴,庆贺他得到的自由,除了夫妇之间的不幸,菲兰达穿着硕长的黑衣服,戴着过时的颈饰,露出不合时宜的傲气,好象过早地衰老了;而穿着鲜艳的天然丝衣服的情妇,恕到被践踏的权利获得恢复,两眼闪着愉快的光彩,焕发了青春。奥雷连诺第二重新投入她的怀抱,象从前跟她睡在一起那么热情,因为当时她把他当成了他的孪生兄弟;跟两兄弟睡觉,她以为上帝给了她空前的幸福——一个男人能象两个男人那么爱她。复苏的情欲是遏制不住的:不止一次,他俩已经坐在桌边,彼此盯着对方的眼睛,一句话没说,遮上餐具,就到卧室里去——两人只顾发泄情欲,饿得要死。
奥雷连诺第二偷访法国艺妓时看见过一些东西,在这些东西的鼓舞下,他给佩特娜·柯特买了一张有帐幔的床,象大主教的卧榻一样,在窗上挂起了丝绒帘子,在卧室的墙上和天花板上都安了挺大的镜子。同时,他比以前更加胡闹和挥霍了。每天早上十一点钟,列车都给他运来成箱的香摈酒和白兰地。奥雷连诺第二从车站上回来时,他都象在即兴舞蹈中那样,把路上偶然邂逅的人拖走——本地人或外来人,熟人或生人,毫无区别。甚至只会说外国话的滑头布劳恩先生,也被奥雷连诺的手势招引来了,好几次在佩特娜·柯特家里喝得酩酊大醉,有一回他甚至让随身的凶猛的德国牧羊犬跳舞,他自己勉强哼着得克萨斯歌曲,而由手风琴伴奏。
“繁殖吧,母牛啊,”奥雷连诺第二在欢宴的高潮中叫嚷,“繁殖吧——生命短促呀。”
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愉快,人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喜欢他,他的牲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控制不住地繁殖。为了没完没了的酒宴,宰了那么多的牛、猪、鸡,院子里的泥土被血弄得乌七八糟、粘搭搭的,骨头和内脏不断扔在这儿,吃剩的食物不断倒在这儿,几乎每小时都要把这些东西哔哔喇喇地烧掉,免得兀鹰来啄客人的眼睛。奥雷连诺第二发胖了,面孔泛起了紫红色,活像乌龟的嘴脸,可一切都怪他那出奇的胃口,甚至周游世界回来的霍·阿卡蒂奥也无法跟他相比。奥雷连诺第二难以思议的暴食、空前未闻的挥霍、无比的好客精神——这种名声传出了沼泽地带,引起了著名暴食者们的注意。许多惊人的暴食者都从沿海各地来到了马孔多,参加佩特娜·柯特家中举行的荒谬的饕餮比赛。奥雷连诺第二是经常取得胜利的,直到一个不幸的星期六卡米娜·萨加斯笃姆来到为止;这个女人体型上很像图腾塑像,是蜚声全国的“母象”。比赛延续到星期二早晨。第一个昼夜,他吃掉了一只小牛,外加配莱:木薯、山药和油炸番蕉,而且喝完了一箱半香摈酒,奥雷连诺第二完全相信自己将胜利。他认为,他的精神和活力都超过沉着的对手;她进食的方式当然是比较内行的,可是正因为这样,就不大使挤满屋子的大部分观众感到兴趣。当奥雷连诺第二渴望胜利、大口咬肉的时候,“母象”却用外科医生般的技术把肉切成块,不慌不忙地吃着,甚至感到一定的愉快。她长得粗壮肥胖,可是女性的温柔胜过了她的茁壮:她有一副漂亮的面孔和一双保养很好的雅致的手儿,还有那么不可抗拒的魅力,以致奥雷连诺第二看见她走进屋子的时候,甚至说他宁愿跟她在床上比赛,而不在桌边比赛,接着,他看见“母象”吃掉了一整条猪腿,一点没有违背进食的礼貌和规矩,他就十分认真他说,这个雅致、惊人、贪馋的女人在某种意义上倒是个理想的女人。他并没有看错,以往传说“母象”是个贪婪的兀鹰,这不是没有根据的。她既不是传说的“绞肉机”,也不是希腊杂技团中满脸络腮子的女人,而是音乐学校校长。当她已经是个可敬的母亲时,为了找到一种能使孩子吃得更多的办法,她也学会了巧妙地狼吞虎咽,但不是靠人为地刺激胃口,而是靠心灵的绝对宁静。她那实践检验过的理论原则是:一个人只要心地平静,就能不停地吃直到疲乏的时候。就这样,由于心理的原因和竞技的兴趣,她离开了自己的学校和家庭,想跟全国闻名的放肆的暴食者决一雌雄。“母象”刚一看见奥雷连诺第二,立即明白他要输的不是肚子,而是性格。的确,到第一夜终了的时候,她还保持着自己的战斗力,而奥雷连诺第二却因说说笑笑消耗了自己的力量。他俩睡了四个小时。然后,每人喝了五十杯橙子汁、八升咖啡,吃了三十只生鸡蛋。第二天早上,在许多小时的不眠之后,吃掉了两头猪、一串香蕉和四箱香槟酒。“母象”开始怀疑奥雷连诺第二不知不觉地采用了她自己的办法,但完全是不顾后果地瞎吃。因此,他比她预料的更危险。佩特娜·柯特把两只烤火鸡拿上桌子的时候,奥雷连诺第二已经快要昏厥了。
“如果不行,你就别吃啦,”“母象”向他说,“就算不分胜负吧。”
她是真心诚意说的,因为她自己也无法再吃一块肉了;她知道对手每吃一口都会加快他的死亡。可是奥雷连诺第二把她的话当成新的挑战,便又吃完了整只火鸡,超过了自己不可思议的容量,失去了知觉。他伏倒在一盘啃光的骨头上,象疯狗似地嘴里流出泡沫,发出临死的稀嘘声。在他突然陷入的黑暗中,他觉得有人从塔顶把他摔进无底的深渊;在最后的刹那间,他明白自己这样掉到底就非死不可了。
“把我抬到菲兰达那儿去吧,”他还来得及说出这么一句。

电影的剧情大概是:战时的下等兵马洛戈瓦伊长相丑陋,生活在机械刻板和长官压制之下,马洛戈瓦伊旺盛的性欲亦受到压制无处释放,便沉浸在偷窥时手淫、以烛火灼皮的猥琐行为和对各种女性的性幻想里,终而恍惚间奸淫母猪尸体并被长官击毙。马洛戈瓦伊与长官妻子偷情而生下长猪尾的儿子卡勒马·巴拉托尼,卡勒马自小被送去练习暴食因此肥胖不堪,而后代表匈牙利参加社会主义暴食大赛,并成为世界冠军,期间结识同为暴食者的妻子,生下儿子拉尤斯·巴拉托尼。拉尤斯是一个极为瘦弱的动物标本匠人,生活主题是制作标本和赡养已肥胖而无法挪动的老卡勒马。最后,拉尤斯将意外死亡的父亲制作成人体标本,并设计一套自动装置,将自己身体切割并制成人体雕像。
从马洛戈瓦伊的欲望受压致死,到卡勒马暴食而肥胖丑陋,到瘦弱的拉尤斯对通俗肉体的极端反感和厌弃,乔治·巴勒菲通过对祖孙三代身体形态异变的串述,呈现了这个“挤压”-“释放”-“迷失”的传奇故事,仿佛吹爆一枚硬气球的过程:拉尤斯和卡勒马残存的尸体成为人体雕像,如同气球爆裂后的碎片,仍然存于世界,供旁观者揣想其历程和意义,但结论似乎只能是虚无——从极端的肉体压制中释放出来,人将迷失于极端的虚胖和虚瘦中。
这种极端状况导致的无尽虚空,在精神上也同样作用于人:马洛戈瓦伊在压制之中,其精神需求和自我感知是极其明确而强烈的,而卡勒马在衣食无忧、精神受到意识形态绑架的生活下,自我仅仅附着于虚华的名利,他存在的内核所剩无几了,直到拉尤斯,他并不生活在表面的物质和精神自由里,而是在父辈和历史的阴影之下,饕餮老父的臃肿肉体和因对这肉体形态的应激性反感而产生的自我否定,让他更失精神内核,陷于虚无及其未知之中,无所依附。自我或精神的完整性在三代人的身上逐渐收缩至无、至死亡的最终领域。
虚无之后,我们将如何看待这个无奈的进程呢?在电影中,拉尤斯和卡勒马的尸体最终被雷古齐教授在地下室里发现,教授将这看作是一项艺术发现,将这一对标本作为艺术品公之于众,并陈述一个看似有所着落的结论:每个人都对什么比较重要有自己的看法,对一些人来说,是空间,对另一些人来说,是时间。
这种堂而皇之的艺术家观念和评价在此显得可笑,它代表的是一种冷漠、麻木的懒惰,在马洛戈瓦伊祖孙三代的经历之中,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感同身受的态度,而非懒散的局外人视角,因为这一夸张而极端的变异,在每一个现代人身上都在或快或慢地发生着,乔治·巴勒菲这部电影的伟大之处,也绝非在题材、艺术手法和讽喻性上,而在他如此形象地描述了一种我们遗忘在历史、忽略于过去而现实存在的问题。
最后说一点扩展:拉尤斯的自我切割装置与小松左京的小说《野性之口》的描述有很大的相似,它着力于以这种极端的设定方法去讨论食欲作为一种人的存在属性的尽头在哪里。另外,卡勒马参加的暴食大赛,让我想起了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对奥雷连诺第二在家中举办饕餮比赛的描写,非常相似。不知道乔治·巴勒菲是否受到了二者的启发。下面附上了这两个文本,感兴趣的话可以读读。
=============================
小松左京《野性之口》:
完全没有理由。
为什么需要一个理由呢?人们总想要为每一件事都找出理由,可真理是永远无法解释的。所有的存在为什么是现存的样态?为什么是以这种方式而不是别的方式存在?
那种理由,还没有任何人可以解答。
他望着窗外磨牙,胸中怒火熊熊。有时候,这种愤怒突然之间就把他淹没了,在他躯体的中心弥漫着一种剧烈的无理性的冲动,一种无法对任何人解释的毁灭的冲动。他猛地拉上窗帘,用力吸气、收紧肩膀,然后回到里屋。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毫无价值、荒谬可笑的。活着是一件荒唐无益的事情。首先,这个毫无价值的玩意儿——我自己——就荒谬得让人无法忍受。
为什么这样荒谬?
“为什么?”——还是这个问题。
毫无价值,荒谬可笑,仅仅因为它就是这样。每件事——财产、科学、爱情、性、生活,老于世故的人——自然、地球、宇宙——所有令人作呕的污秽,让人沮丧的愚蠢。所以——
不。根本不是所以,而是无论如何,我真的要去做那件事。
我要去做。他无声地喊:我确实要。
当然,这将和别的事一样愚蠢——事实上,在一切各式各样的蠢事中间,也许是最愚蠢的?但至少这件事有那么一点刺激——一种锐利的感觉。也许这个详细周全的计划的核心就是一种疯狂的尝试?也许是这样,但至少——
我就要开始做的这件事是任何人在头脑正常的时候从未尝试过的。
毁灭世界?历史上有千千万万人有过这样的狂想。而他这个想法不是那么陈旧的。不可能有更荒谬的想法了,只有它才能扑灭他心头的怒火。我内心的火焰被一种高贵的绝望扇起来了……
进入内室,他锁上门,打开灯。现在——这想法使他两眼放光——现在开始了。
清冷的光线照亮了房间。一个角落里摆着一台家用电烤箱;一组煤气灶、一部切片机、大大小小的平底锅、一套刀具、一个装满各种调味料和蔬菜的壁橱。旁边是一个自动工作台,设置了全套程序,可以进行人类有史以来对身体进行过的任何外科手术——不管是难度多大、多么复杂的手术,即使是最大的医院里才能做的,这里也都能完成。手术台旁边,是一些假肢:手、脚;任何一种最先进的人造器官。
万事具备。他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去策划细节,又花了一个月准备工具。据他推算,作好全部准备至少又多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好,那么——让我们开始吧。
他脱下裤子,爬上手术台,把控制器的许多电极接在身上,扭开摄像机。
开始了——
他用一种戏剧化的姿势拿起手术台支架上的注射器,检查压力刻度,调整设置——调高了一点,因为这是第一次注射——然后把禁用的麻醉剂注射进他右大腿。
大约过了五分钟,这条腿完全失去了知觉,他扭开了自动手术机。机器运作时吱吱呜呜的声音;自动指示灯熄熄亮亮;他的身体不由自主被向后猛拉,同时黑色的机械手延伸出 多个分支。
桌上凸出的夹子固定住腿的胫部和足踝 。一只钢爪握着一个消毒纱布包往下滑到大腿和骨盆的连接处。
电子解剖刀如丝一般细细地切过皮肤,所过之处非常炽热,几乎没有鲜血流出。切开肌肉组织……露出大动脉……用钳子把肉夹下来……包扎……切除并处理感染的肌肉表面……嗡嗡叫着的轮转机锯条旋转着切向股骨。锯条切中了骨头,那一刹那他闭上了眼睛。
几乎没有什么震动感。当内置钻石头的超高速锯条切过骨头时,只发出了轻微的摩擦声,同时给骨头切面敷上混合的强力酵素。在精确的6分钟内,他的右腿干净利落地同躯干分离了开来。
机器用纱布擦拭他浸透汗水的脸,然后递给他一杯药水。他把药水一口饮尽,深吸了口气。他的脉搏在飞快地上升,更多汗水如雨般涌出。但几乎没有失血,也没有什么近似疼痛的感觉。神经治疗很管用。不需要输血。他吸了一些氧气,以缓解头昏眼花的症状。
他那条和身体分离的右腿直挺挺躺在床上。透过透明塑料的绷带,可以看到:一圈外围包着黄色脂肪的收缩的粉红色肌肉组织、白色的骨骼中心可见黑红色的骨髓。几乎没有流血。他望着这条膝盖骨突出的毛绒绒的玩意,几乎忍不住要歇斯底里地狂笑起来。但是此刻没有笑的时间:还有更多的事需要做。
他休息了片刻以恢复体力,然后发出下一步工作的指令。
机器伸出一条机械手,抓起一条人造腿,把它安在刚才的切割面上;没有扎绷带的肌肉上药以后已经恢复了。人工突触中心的信息终端被与从切割处拉出来的神经叶鞘连在一起。终于,躯干的义肢被用带子和特殊医疗器械牢牢安在残余的大腿骨上。完成了。他试着小心地弯曲这条新腿。
到现在为止一切顺利。他极其小心地站起来:变化使他头昏、摇摇晃晃,但不管怎么说他可以站立也能慢慢走路了。假腿是用某种运动时声音很细微的轻金属制成的。没问题——够好的了——反正大部分时间里他都会坐轮椅的。
他举起自己的右腿从桌子头上放下去。腿太沉,几乎使他蹒跚了一下。他又一次在心里爆发了一阵野蛮的狂笑。我整个一生中一直拖着这些分量来来去去。切下这个肢体使他减轻了多少公斤的体重呢?
“好吧,”他咕哝着说,还在咯咯笑,“够了。现在该把血排干净了。”
他把这一大块肉扛上操作台,剥掉塑料包装,系住脚踝倒吊在天花板上,用他的双手挤压,从切口处放血。
后来,在洗涤槽里冲洗它的时候,上面的毛被水敷湿了,在所有动物的肢体中,它看上去最像一只巨大的蛙腿。他瞪着以古怪的姿势戳出不锈钢洗涤槽的那只脚的脚底心。
我的腿。凸出的膝盖,很难找到合脚鞋子的高脚背,一只运动员的脚上生的脚趾——这是我的腿!他终于再也忍不住了,爆发出一阵恶毒的狂笑,在笑声中痉挛地折起腰。最后,这只见鬼的坚韧的运动员的脚终于完蛋了……
是准备烹调的时候了。
他用大切片刀把这条腿从膝部切成两截,然后开始用一把锋利的猪肉刀剥皮。大腿骨裹着看上去很可口的肉,很是粗壮。当然,这是火腿。筋腱很有韧性;他用硬切片刀切得大汗淋漓,很快在身边垒起了厚厚的带着肌肉膜的肉块。他把大块胫骨处的肉放进装满滚水的大罐子,加上桂皮、丁香、芹菜、洋葱、茴香、藏红花、胡椒粒、其他调料和辛辣的蔬菜一起炖。脚被他丢掉了,只从足踝处刮了些肉下来。他把腿肉中用来做肉排的都切了片、擦了盐和胡椒,并拍打肉片使它们变软。
我会有勇气吃它吗?他突然问自己。结实的肉团总会梗在他咽喉的某处。他真的能够把它咽下去吗?
他咬紧牙关,油一般的汗水流了下来。我会吃的。这和人类一直以来烹制并享用其他有智慧的哺乳动物没有什么不同:母牛和绵羊,那些温和的,无辜的,有着悲伤眼睛的食草动物。原始人甚至吃自己的同类;有些种族直到现代还延续着吃人的习俗。为了吃而杀掉动物——也许这中间有正当的理由。其他食肉动物也不得不靠杀戮生存。但是人类……
从他们存在的那一天起,贯穿人类历史,有多少亿万人被杀掉而连吃也没有吃?和那个相比,这样绝对是清白无罪的。我将不去杀任何别的人。我不会去屠杀可怜的动物。通过这种方法,我自己吃的是我自己的肉。还有哪种别的肉能像这种一样毫无罪过?
煎锅里的油开始噼啪作响。他用颤抖的手抓起一大块肉排,犹豫片刻,把它丢进锅里。噼啪响的脂肪使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香喷喷的味道。他仍在发抖,他把轮椅把手握得太紧,几乎要把它折短了。
好吧。我是一只猪。或者,人类比猪要糟糕得多:卑鄙,污秽。在我体内有个部分比猪还不如,还有个“高贵”的部分为比猪还不如感到无尽的愤怒。那个高贵的部分将把那比猪还不如的部分吃掉。这件事里有什么让人害怕的东西么?
被烤得金黄松脆的肉排在盘子上滋滋作响。他往上面抹了芥末,配上柠檬和奶油,浇上肉汁。他拿起餐刀的时候,他的手在打颤,餐刀敲在盘子上,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他汗如雨下,用尽全力握住餐刀,切割,用叉子戳起来,然后提心吊胆地把它送进嘴里。
第三天,他截下了左腿。这一只,胫骨和全部表面都被抹上了大量奶油,用烤肉叉叉起来,架在旋转型烤肉架上烤了。至此他已不再恐惧。他发现自己惊人的可口:这个发现使一种混合着愤怒和疯狂的情绪在他心底牢牢扎下了根。
第一周以后,事情越来越艰难了。他不得不切断了自己的下半身。
在轮椅的方便马桶上,他最后一次享受了排泄的乐趣。当他喷射的时候,他大笑了。
看看这肮脏的货色!我排泄的是我自己,在我自己的内脏中储存然后变成粪便!也许这是自我蔑视的最高形式了——或者是自我颂扬的最高形式?
当他失掉了髋骨以下的部分,两条假腿就基本没用了。但他还让它们留在老地方。现在是换下内部器官的时候了,他向机器的电脑咨询:“当我把肠子吃掉之后,还会有食欲吗?”
“它不会受什么影响。”这就是回答。
他抛掉了大肠,把小肠和蔬菜一起炖,把十二指肠做成腊肠。他用人造器官换下了肝脏和肾脏,然后把这两个器官做了小炒。肚子他先放在一边,放在装着营养液的塑料容器中保存。
在第三周的末尾,他换下了他的心和肺,最后,他把自己跳动的心切成细丝油煎:这是连阿兹塔克主持献祭的祭师都无法想象的事情。(注:阿兹塔克人:16世纪西班牙人入侵时期生活在墨西哥中部的印地安人部族)
当他开始把自己的腹部做成餐点时,他开始清醒地意识到:人类是可以在毫无食欲的情况下机械进食的。腹部用酱油浸泡着,加上了大蒜和红辣椒。
在无数各种各样、希奇古怪的被当作食物的产品中,有多少完全与饥饿无关、纯粹是由于好奇而被开发的?即使好奇心得到了满足,人类还是会吃最不可思议的东西,如果他感到饥饿。吃自己同类的肉时,那种愤怒的感觉就像是用牙齿咬碎玻璃杯一样。
食欲的源泉来自于原始的侵略冲动:杀戮和吃食;践踏和粉碎;吞咽和吸收
——那就是野性之口。
到现在,他的咽喉只能与一根管子相连。直接输送到血液的营养来自一个装满营养液的容器。内分泌活动由人造器官完成。在这张嘴的尽头,双臂都被吃完;唯一保留的是颈部以上的部分,而在第五十天头上,面部所有的肌肉几乎都被吃光了;剩下两片嘴唇在安装的弹簧支持下咀嚼。眼球只剩一只,另一只被吞进嘴里嚼掉了。
现在坐在轮椅上的,是和错综复杂的大大小小的管子堆在一块儿的一副骨架,在这副骨架上,唯一留存的是大脑和一张嘴巴。
不……
即使是现在,一只机械手臂正在剥去头皮,用锯条把头盖骨的顶部干净利落地切了下来。
在暴露的小脑上撒上盐巴、胡椒粉和柠檬汁,舀起满满一大勺——我的脑子,想到这是我的小脑。我怎么能尝这个东西呢?难道一个活人能够品尝自己脑浆的滋味吗?
勺子毁坏了灰色的大脑。没有痛苦——大脑皮层没有感觉。但到了这时,机械手舀出一勺勺灰色糊状的东西放到骷髅的嘴里,嘴巴贪婪地吞咽下去时,“味道”已经无法辨别了。
“是杀人案。”警官从屋里走出来时,面对挤满出口处的记者们说,“此外,这是一起残忍、野蛮得难以想象的罪行。罪犯无疑是一个严重的精神病患者。看上去像是某种变态的实验——身体被一块块卸下来,然后装上人工器官……”
警官处理好媒体方面的问题,进了屋,擦去脸上疲惫的汗水。
从焚化炉过来的侦探疑问地看着他。“录像带已经烧毁了,”他说,“但是,你为什么要说这是一次谋杀呢?”
“为了维持社会的美好与和平。”警官做了个深呼吸。“把它宣布为谋杀——指挥一次官方的调查——然后让它成为我的秘密。这次案件——抹去案件中的证据——它们完全是不合常理的。你不能让一个正常的市民看到在一些人心灵深处的疯狂和自我毁灭的欲望。如果我们做了这样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不小心让人们看到了内心寄居的原始的野兽——好吧,你可以肯定会有人学这个人的样。这一种人——你没办法知道他们能做出什么……
“如果广大民众突然了解了这样的东西,人们将对自己的行为失去自信——他们会开始钻入自己灵魂深处的黑暗中。他们会彻底无法理解自己——完全失去控制!
“你看,人类存在的根源是疯狂——所有动物心底的那种盲目的侵略性的冲动。如果人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果有大批人用存在解放或自己管自己之类的口号来表达这种疯狂——那就是人类文明的终结。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法律、武力、或规章来约束,一切将完全失控!
“人们把别的人撕碎,互相残杀,破坏、毁灭,这些征兆已经开始显现——这个人吞下融化的炸药自杀——那个人倒上汽油自焚而死——另一个光天化日之下在城市中心性交。当没再有什么理智的行为可以作为攻击对象,笼中的野兽就开始毁灭自己的心智——”
“啊呀——”
年轻的侦探从正在腐烂的骨架旁跳开。刚才,正当他想把仍然塞在骷髅嘴里的恶臭的勺羹取出来时,那骷髅的牙齿扣下来,咬住了他的食指,咬掉了指尖的一小块肉。
“小心呀,”警官疲惫地说,“一切动物生命的根基就是那张带着如饥似渴的吞噬欲望的嘴巴,巨大的野性之口……”
在那具裸露着大脑的骷髅上,残留的一只眼球开始变松,有力的弹簧替代了消失的肌肉,正在用肿胀的舌头和坚硬的牙齿咯吱咯吱地咀嚼着那块小小的肉屑。
《百年孤独》对于奥雷连诺第二暴食的描写:
家中的生活变得那么严峻,奥雷连诺第二就觉得在佩特娜·柯特家里更舒服了。首先,他借口减轻妻子的负担,把酒宴移到了情妇家里。然后,借口牲畜正在丧失繁殖力,他又把畜栏和马厩迁到她那儿去了。最后,借口情妇家里不那么热,他甚至把经营买卖的小账房搬到了那儿。菲兰达发现自己变成了守活寡的妇人,时间已经迟了。奥雷连诺第二几乎不在家里吃饭,只是假装回家过夜,但这是骗不了人的。有一天早晨他不小心,有人发现他在佩特娜·柯特床上,然而出乎意外,他不仅没有听到妻子的一小点责备,甚至没有听到她最轻微的怨声,但是就在那一天,菲兰达把他的两口衣箱送到他的情妇家里。她是叫人大白天经过街道中间送去的,让全镇的人都能看见,以为不走正道的丈夫忍受不了耻辱,会弯着脖子回到窝里,可是这个勇敢的姿态只是再一次证明,菲兰达不熟悉丈夫的性格和马孔多的风习,这里的习俗和她父母的旧习毫无共同之处——每一个看见箱子的人都说,这是故事的自然结局,故事的内情是人人皆知的。奥雷连诺第二却举办了三天的酒宴,庆贺他得到的自由,除了夫妇之间的不幸,菲兰达穿着硕长的黑衣服,戴着过时的颈饰,露出不合时宜的傲气,好象过早地衰老了;而穿着鲜艳的天然丝衣服的情妇,恕到被践踏的权利获得恢复,两眼闪着愉快的光彩,焕发了青春。奥雷连诺第二重新投入她的怀抱,象从前跟她睡在一起那么热情,因为当时她把他当成了他的孪生兄弟;跟两兄弟睡觉,她以为上帝给了她空前的幸福——一个男人能象两个男人那么爱她。复苏的情欲是遏制不住的:不止一次,他俩已经坐在桌边,彼此盯着对方的眼睛,一句话没说,遮上餐具,就到卧室里去——两人只顾发泄情欲,饿得要死。
奥雷连诺第二偷访法国艺妓时看见过一些东西,在这些东西的鼓舞下,他给佩特娜·柯特买了一张有帐幔的床,象大主教的卧榻一样,在窗上挂起了丝绒帘子,在卧室的墙上和天花板上都安了挺大的镜子。同时,他比以前更加胡闹和挥霍了。每天早上十一点钟,列车都给他运来成箱的香摈酒和白兰地。奥雷连诺第二从车站上回来时,他都象在即兴舞蹈中那样,把路上偶然邂逅的人拖走——本地人或外来人,熟人或生人,毫无区别。甚至只会说外国话的滑头布劳恩先生,也被奥雷连诺的手势招引来了,好几次在佩特娜·柯特家里喝得酩酊大醉,有一回他甚至让随身的凶猛的德国牧羊犬跳舞,他自己勉强哼着得克萨斯歌曲,而由手风琴伴奏。
“繁殖吧,母牛啊,”奥雷连诺第二在欢宴的高潮中叫嚷,“繁殖吧——生命短促呀。”
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愉快,人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喜欢他,他的牲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控制不住地繁殖。为了没完没了的酒宴,宰了那么多的牛、猪、鸡,院子里的泥土被血弄得乌七八糟、粘搭搭的,骨头和内脏不断扔在这儿,吃剩的食物不断倒在这儿,几乎每小时都要把这些东西哔哔喇喇地烧掉,免得兀鹰来啄客人的眼睛。奥雷连诺第二发胖了,面孔泛起了紫红色,活像乌龟的嘴脸,可一切都怪他那出奇的胃口,甚至周游世界回来的霍·阿卡蒂奥也无法跟他相比。奥雷连诺第二难以思议的暴食、空前未闻的挥霍、无比的好客精神——这种名声传出了沼泽地带,引起了著名暴食者们的注意。许多惊人的暴食者都从沿海各地来到了马孔多,参加佩特娜·柯特家中举行的荒谬的饕餮比赛。奥雷连诺第二是经常取得胜利的,直到一个不幸的星期六卡米娜·萨加斯笃姆来到为止;这个女人体型上很像图腾塑像,是蜚声全国的“母象”。比赛延续到星期二早晨。第一个昼夜,他吃掉了一只小牛,外加配莱:木薯、山药和油炸番蕉,而且喝完了一箱半香摈酒,奥雷连诺第二完全相信自己将胜利。他认为,他的精神和活力都超过沉着的对手;她进食的方式当然是比较内行的,可是正因为这样,就不大使挤满屋子的大部分观众感到兴趣。当奥雷连诺第二渴望胜利、大口咬肉的时候,“母象”却用外科医生般的技术把肉切成块,不慌不忙地吃着,甚至感到一定的愉快。她长得粗壮肥胖,可是女性的温柔胜过了她的茁壮:她有一副漂亮的面孔和一双保养很好的雅致的手儿,还有那么不可抗拒的魅力,以致奥雷连诺第二看见她走进屋子的时候,甚至说他宁愿跟她在床上比赛,而不在桌边比赛,接着,他看见“母象”吃掉了一整条猪腿,一点没有违背进食的礼貌和规矩,他就十分认真他说,这个雅致、惊人、贪馋的女人在某种意义上倒是个理想的女人。他并没有看错,以往传说“母象”是个贪婪的兀鹰,这不是没有根据的。她既不是传说的“绞肉机”,也不是希腊杂技团中满脸络腮子的女人,而是音乐学校校长。当她已经是个可敬的母亲时,为了找到一种能使孩子吃得更多的办法,她也学会了巧妙地狼吞虎咽,但不是靠人为地刺激胃口,而是靠心灵的绝对宁静。她那实践检验过的理论原则是:一个人只要心地平静,就能不停地吃直到疲乏的时候。就这样,由于心理的原因和竞技的兴趣,她离开了自己的学校和家庭,想跟全国闻名的放肆的暴食者决一雌雄。“母象”刚一看见奥雷连诺第二,立即明白他要输的不是肚子,而是性格。的确,到第一夜终了的时候,她还保持着自己的战斗力,而奥雷连诺第二却因说说笑笑消耗了自己的力量。他俩睡了四个小时。然后,每人喝了五十杯橙子汁、八升咖啡,吃了三十只生鸡蛋。第二天早上,在许多小时的不眠之后,吃掉了两头猪、一串香蕉和四箱香槟酒。“母象”开始怀疑奥雷连诺第二不知不觉地采用了她自己的办法,但完全是不顾后果地瞎吃。因此,他比她预料的更危险。佩特娜·柯特把两只烤火鸡拿上桌子的时候,奥雷连诺第二已经快要昏厥了。
“如果不行,你就别吃啦,”“母象”向他说,“就算不分胜负吧。”
她是真心诚意说的,因为她自己也无法再吃一块肉了;她知道对手每吃一口都会加快他的死亡。可是奥雷连诺第二把她的话当成新的挑战,便又吃完了整只火鸡,超过了自己不可思议的容量,失去了知觉。他伏倒在一盘啃光的骨头上,象疯狗似地嘴里流出泡沫,发出临死的稀嘘声。在他突然陷入的黑暗中,他觉得有人从塔顶把他摔进无底的深渊;在最后的刹那间,他明白自己这样掉到底就非死不可了。
“把我抬到菲兰达那儿去吧,”他还来得及说出这么一句。

4 ) 魔幻现实主义即是人性私处的巧妙解剖
你是一个性压抑的丑八怪
用蜡烛灼伤肌肤
在鸡巴上燃烧出孤独的火焰
然后淋上寒冬的冰水浇灭欲望
现实是一把早已扣动扳机的暗枪
偷窥,自慰,兽交
所有隐秘的空虚被释放
产物在秘密遗传
暴食,野合,利欲
继承者无师自通
畸形,懦弱,孤僻
终结者从来无法终结任何恶德
这是一个冷漠的年代
而你只是别人眼里
千千万万个故事中早晚会忘记的那一个
用蜡烛灼伤肌肤
在鸡巴上燃烧出孤独的火焰
然后淋上寒冬的冰水浇灭欲望
现实是一把早已扣动扳机的暗枪
偷窥,自慰,兽交
所有隐秘的空虚被释放
产物在秘密遗传
暴食,野合,利欲
继承者无师自通
畸形,懦弱,孤僻
终结者从来无法终结任何恶德
这是一个冷漠的年代
而你只是别人眼里
千千万万个故事中早晚会忘记的那一个
5 ) 一部需要思考的电影
要不是有朋友的推荐,
要不是已经事先看过剧情的简介,
我想我是不可能喜欢上这么一部戏的,
然而,它的确有吸引我的能力。
三代人的命运各有不同,他们为了自己心里面的追求,
至死方休。
极端的渴望性,
极端的渴望赢,
极端的渴望成为艺术品……
人生是由很多的坚持甚至是偏执所组成的。
倘若他们不再这样偏执,或许他们的生活会正常很多,或许他们也会像你我今天一样默默无闻。
也许,执着两个自本来就是可怕的,
有如片子开头那个喷火的阴茎一般,
让人害怕又不自觉的发出赞叹。
要不是已经事先看过剧情的简介,
我想我是不可能喜欢上这么一部戏的,
然而,它的确有吸引我的能力。
三代人的命运各有不同,他们为了自己心里面的追求,
至死方休。
极端的渴望性,
极端的渴望赢,
极端的渴望成为艺术品……
人生是由很多的坚持甚至是偏执所组成的。
倘若他们不再这样偏执,或许他们的生活会正常很多,或许他们也会像你我今天一样默默无闻。
也许,执着两个自本来就是可怕的,
有如片子开头那个喷火的阴茎一般,
让人害怕又不自觉的发出赞叹。
6 ) 視覺挑戰
導演說 "Tell something important about yourself."
這是三代的故事:祖父、父、子;也是三個故事,三位主角畢生追求:慾、名利、永恆。並且追到上腦,幾乎每分每刻都是為著單一的目標而活動、而生活。祖父那一代,(不知道是下屬還是奴隸),看見任何東西都可自慰,即使對象是一頭死豬;父天生有一條豬尾,雖然祖父已狠狠地剪斷它,父的身形也如豬一樣--不斷地吃,吃完吐,吐完吃,沒完沒了,為的是勁食大賽金牌;兒子很專業,對著各樣失去脈搏的動物,專心地做標本,起死回生,最後做的標本,就是自己,「永垂不朽」的身體。
嚇死人!明知道戲中切開的,是豬肉,拿出來的,是豬內臟,但還是救命!不得不閉上眼。亦因為閉上眼,更留意到戲院觀察的動靜。當然是鴉雀無聲,間中有些「咦」「Wo」「Ush」有些人買了汽水,但沒動過,大家都屏息靜氣。雖然核突,但又忍不住要看,很想知道之後是怎樣,會得到什麼結局。看著,也聯想到:在扶手梯底下向上目不轉睛的男人、用牙刷扣喉減肥的女人、Damien Hirst的死牛。有些極其嘔心讓人不明白的事情其實每天都在發生。
這是三代的故事:祖父、父、子;也是三個故事,三位主角畢生追求:慾、名利、永恆。並且追到上腦,幾乎每分每刻都是為著單一的目標而活動、而生活。祖父那一代,(不知道是下屬還是奴隸),看見任何東西都可自慰,即使對象是一頭死豬;父天生有一條豬尾,雖然祖父已狠狠地剪斷它,父的身形也如豬一樣--不斷地吃,吃完吐,吐完吃,沒完沒了,為的是勁食大賽金牌;兒子很專業,對著各樣失去脈搏的動物,專心地做標本,起死回生,最後做的標本,就是自己,「永垂不朽」的身體。
嚇死人!明知道戲中切開的,是豬肉,拿出來的,是豬內臟,但還是救命!不得不閉上眼。亦因為閉上眼,更留意到戲院觀察的動靜。當然是鴉雀無聲,間中有些「咦」「Wo」「Ush」有些人買了汽水,但沒動過,大家都屏息靜氣。雖然核突,但又忍不住要看,很想知道之後是怎樣,會得到什麼結局。看著,也聯想到:在扶手梯底下向上目不轉睛的男人、用牙刷扣喉減肥的女人、Damien Hirst的死牛。有些極其嘔心讓人不明白的事情其實每天都在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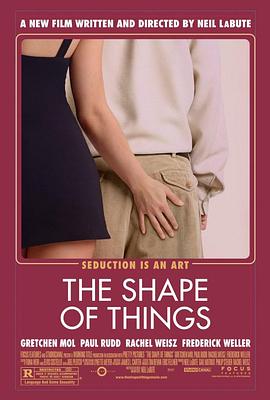




















仅浴盆如沙漏般旋转带出时代变迁一幕,就足以让我惊叹,神作!
这才是魔幻现实主义!这才是神作!《铁皮鼓》弱爆了!《地下》是儿童电影么!《南方》根本就是屎!导演György Pálfi是天才!加上Amon Tobin的原声!看完全身细胞都是兴奋的!
有点恶心,不过能承受.最后的镜头实在经典!
.............。
9.1;这样拍下去György Pálfi非成精不可,看来我需要恶补历史
迄今为止看过的唯一一部带有马尔克斯气质的魔幻现实主义电影
高超的手法,险恶的用心
太...抽象這樣的電影往往承載了太多的象徵還有不滿... 這是值得挑戰的電影最後父子變成標本而且在潔白的廳堂里一裙木訥的人給我的感覺很壓抑
另类到极致,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喜欢精液血液的可以看一下,因为太过古怪了,可以说很好也能说很差,所以不予评分!据说能看完的人不多……
相当好看,我有必要推荐,当年为了这片儿翘掉了物理还是化学实验
性欲,暴食,人体标本
魔幻社会主义。
「个人的是政治的,政治的是戏剧的」。非常马尔克斯。祖孙三代怪诞嬗变演绎畸形东欧政权。血液喷张,兼具黑色幽默。当然也可以列作top10邪典片。
三次差点吐了……那个旋转镜头的大澡盆蒙太奇太棒了
比肩火烈鸟的戛纳另类极品
魔不幻,寫不實。
快进没看明白,静下心来重看再评分
三段式,好TMD重口味。不是帕索里尼式的而是杨斯凡克梅耶式的……视听语言上是大量特写的剪辑,以及奇诡的运动镜头和角度。除了食色,人还追求超越——所谓的木乃伊情结。这部片子大约没有胃口再看第二遍……但是它着实NB。
消解性欲、消解食欲、消解身体,魔幻主义,马尔克斯的影响随处可见。
荒诞并且恶心的电影